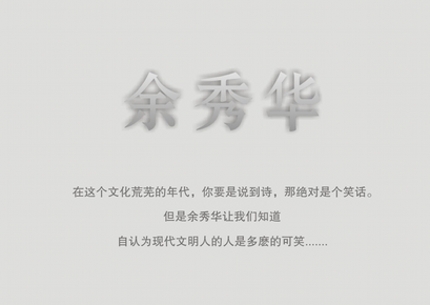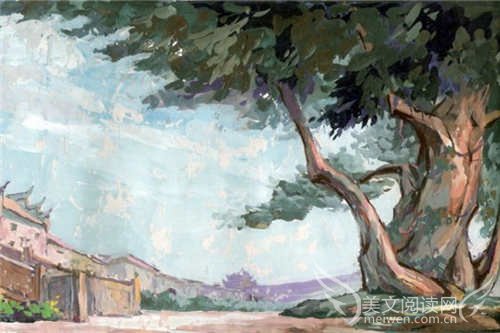网络使中国文化改朝换代
但愿网络文学的“传销”、“直销”不仅掀起某些作品的热读,也能使原本高处不胜寒的文学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获得更大范围的延续。
博客的发明,有点像“傻瓜相机”,因其廉宜及易于操作,使人人皆可成为摄影师,技术的平民化造成艺术的大众化。
博客的发明,又有点像卡拉OK,爱好者们不再仅仅坐在听众席上,也能拿到话筒,自弹自唱、自娱自乐,体验一番当歌手的快感。艺术要流行,重在参予——重在给予别人参予的机会。
博客的发明,又有点像“海选”,从茫茫人海里选美:选美声、选美人、选美文。看谁能回眸一笑百媚生,使三千粉黛无颜色。吸引的眼球都是充满梦想的眼球: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每位参予者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正如谚语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网络文学的战场上,“不想当偶像的粉丝不是好粉丝”。
最好的读者是作者,最好的作者注定又是从读者中产生的,有数量越大的读者,也会有影响越大的作者——博客就是这样水涨船高地造英雄。
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异军突起,把原本以纸媒为主要载体的所谓“纯文学”给架空了,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而对网络文学越来越丰厚的群众基础,纯文学体会到大权旁落的感觉,却又自欺欺人地以太上皇自居。网络使文学改朝换代。
网络造成并扩大了文学的代沟。80后、90后,大多把上网作为阅读的主要手段。而严肃文学大多通过纸媒体传播。这意味着它很难在80后、90后中培养起大批铁杆粉丝。纯文学乃至纯文学书刊的日暮途穷,即由此而来,纯文学面临着断代、割裂的危机。一种文学品质、一种文学风格,如果失去大批拥戴者,还可以小众化的形式生存;可如果找不到得力的接班人,则意味着它不仅很难重振雄风,还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八十年代腾空而起的纯文学,二十多年来路越走越窄,不仅失去了市场的号召力,还未得到新媒体的青睐,甚至日渐被网络文学驱逐、挤压、遮蔽,现在主要靠原有的体制(譬如文联、作协系统的期刊及某些奖励机制)给支撑着。当然,许多纯文学作家耐得住寂寞,安贫乐道的觉悟与境界,也为之保留并延续着理想主义的火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莫非中国文学,文学的作者与读者,真的出现了无法弥合的代沟?莫非纯文学变成了老化的文学、垂死的文学?莫非纯文学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失去话语权的遗老遗少?
孙中山当年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网络文化真的代表世界新潮流吗?纯文学与网络文学真的南辕北辙,相背而行吗?
网络时代的到来,给旧文学即所谓纯文学提出很多问题,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不见得是坏事。如果没有这新潮、新新潮冲击,曾经被八十年代的胜利冲昏头脑的纯文学,还自以为很新潮呢,还意识不到自己落伍了呢。“桃花源”里的纯文学作家,还在为争当夜郎国的国王吵闹得不可开交呢。网络的重新洗牌,使他们如梦方醒:“桃花源”不过就是—“水帘洞”,美猴王离开自己的山寨,不过就是一贩夫走卒。所有贵族般的清高与骄傲,都是虚拟的,比网络还要虚拟。
文学,包括纯文学,说白了还是要靠圈外的读者买账,才真正有效。没有读者的文学,读者不爱读的文学,尤其是无法让读者感动的文学,作者自己再当回事,也注定是无效的。
原先的纯文学里,小说、散文、评论,都因为网络文学的新兴勃起,而显得老态龙钟,连以先锋自命的现代派都眨眼间变成了旧货,反倒是在纯文学里原本就很边缘化的诗歌,与网络一拍即合。不仅没有继续衰落,反而借网络之东风扶摇直上。
为什么诗歌就不怕网络的遮蔽,反而得网络之助闪耀登场,重新亮相呢?这证明了诗歌真有一种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精神。而其它纯文学样式,常常是所谓的纯文学,其实并不纯,或者说没纯到家,没纯到极致,若真纯到极致就死不了的。
网络上那么多人在议论“文学死了”,却没人敢说“诗歌死了”。谁都知道,诗歌是死不掉的,一方面因为中国自古即是诗国,有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另一方面,中国诗人早就学会了自救。市场经济的物质主义,都没把诗歌的海市蜃楼挤垮,都没把中国诗人全饿死,网络的铺天盖地,难道就能把诗人给淹死吗?他们早就学会游泳了,不,他们天生就会水性,在最严酷的环境里都能存活,尤其擅长绝处逢生,无空不入。
诗歌注定是文学的急先锋与轻骑兵。它凭着嗅觉就能闻到网络时代蕴含的无限生机。它一开始就是张开双臂拥抱网络的。果然,网络使诗歌插上翅膀,使诗人的交流更为密切,仿佛回到盛唐。中国诗歌的现场,以最快的速度由纸媒体转移到网络上,捷足先登。不,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诗人们就懂得以自费诗集、民办报刊、朗诵会来弥补官方诗刊阵地有限之不足了。
诗歌是讲究行动的文学,是注重现场的文学,是真正的纯文学。超越功利,无欲则刚,是真正活着的文学。网络的出现如同天意,使诗歌枯木逢春,迎来了自八十年代之后的又一个青春期。诗人比那些功利性的作家更无私,更愿意奉献,也更勇于牺牲,所以也就更适应网络时代:诗歌是一棵树,只要有一块土壤,就想开花结果,难道开花还需要理由,难道结果还想到收版税吗?
写诗是为了自娱并娱人的,这与网络的魅力不谋而合。许多人上网,不就是为了说话吗?有一点话语权就够了。不是为了把自己的话卖个好价钱的。诗人写诗也是如此。所以无求功利的诗歌通过网络找到更多情投意合的读者。所以无私的诗人,无意插柳柳成荫,在网络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如果网络制造的文学革命,确实相当于焚书坑儒,那它肯定无法把诗歌付之一炬,因为诗歌不是死书,诗歌是活着的;网络革命埋没的腐朽儒生中,肯定不包括诗人,因为诗人不是读死书、死读书长大的。诗人是斗士,诗人拥抱新潮流,因为诗人永远比任何新潮还要新潮。诗人自古至今都是思想与情感的潮人。
对于21世纪初的中国诗人来说,网络来得正是时候。这场急时雨使诗歌枝繁叶茂。网络诗歌还将载入诗歌史——不,网络改变了中国诗歌,也改变了中国诗歌史。现在,是网络诗人,是网络诗歌,在领风骚了。不可想象:一位拒绝网络的诗人,或一位被网络拒绝的诗人,能成为当代的李白。相反,李白若活在今天,他会开博客的,他不会哀叹怀才不遇、知音难觅,网络的发达与便捷,使他不用责怪蜀道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