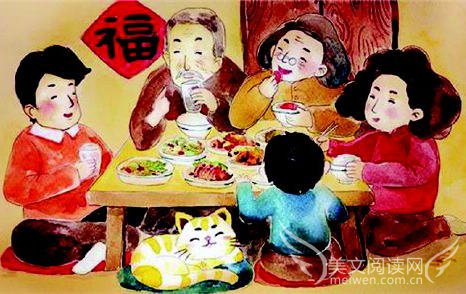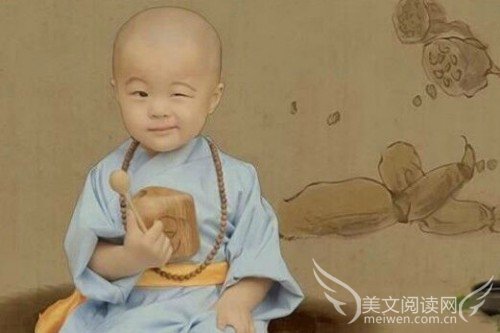年的味道(散文)
我们那儿杀猪的师傅多是请来的,也会劁猪骟羊,以此为营生。师傅着道褂,掂牛耳尖刀,在磨刀石上磨得寒光闪闪,用手试了试刀锋后,向汉子们挥了挥手说,逮猪!
圈里养着一头大肥猪,少说也有三百来斤,它还在无忧无虑地吃着猪食,不知道危险就在眼前。见几个汉子进了猪圈向自己包抄过来,它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发出哼哼唧唧的叫声,晃动着笨拙的身躯躲避着人。人越是赶它,出于本能,它越跑得急。看起来猪并不完全笨,这么大的猪要想逮住摁倒还真不容易,几个汉子大冷天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时间一久,猪也累了,汉子们一拥而上,将它摁倒在地,四脚用绳结结实实地捆了,这猪便嗷嗷地叫,似乎感觉到末日的到来。
汉子们用杠子把猪抬出猪圈,放在指定的位置。杀猪的师傅吩咐汉子们摁住猪,有摁头的,有摁尾的,还有摁腿的。只见杀猪的师傅嘴里噙住刀背,用左腿膝盖顶住猪的前身,右脚蹬实地面,手攥紧了刀柄,用力刺向猪的脖子,一道红光喷出,有人急忙用盆接住,那猪的惨叫声便不绝于耳,尔后慢慢消失……
杀好了猪,汉子们再把它抬进滚滚的大锅里烫毛,经过滚水的浸泡,猪毛很快被褪掉。
把猪挂在铁钩子上,杀猪师傅用刀在猪身上来回地刮,一丝不苟,把残留的猪毛及秽物一起清理掉,直刮得猪身子白白净净、光光溜溜的。乡亲们便围过来,说说笑笑,指指点点。有的挑肥,有的拣瘦,有的要肝,有的要肺,还有要猪头肉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个二斤,那个三斤,一阵子卖个精光。乡亲们各自掂着猪肉,带着孩子,哼着小曲,回家准备过大年去了……
当然,主家不会亏了杀猪的师傅,好酒好肉地招待一番。临走,还要奉上两盒黄金烟,两块钱的佣费。
贴春联
春联,俗称门对子,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最大众化的活动。春联起源于古代的桃符,有着悠久的历史。
宋代诗人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写了宋代人过春节辞旧迎新的场面,也是一幅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民间风俗画卷。
贴春联是有讲究的。春联的内容要与家庭情况相协调;上联贴右,下联贴左。仄尾者为上联,平收者为下联。
年三十吃了早饭,爷爷清扫了门板周围,便督促我帮着贴春联。母亲先烧开了水,把面粉洒在里边,用筷子快速地搅动,一会打好了浆糊。爷爷把春联摊平,用秫秸亭子蘸上粘粘的浆糊,在春联的背面上下左右地抹上几遍,然后让我掂着站在凳子上张贴。
爷爷戴着羊皮帽,穿着棉袍,腰间裹得紧紧的,再系根粗布带子。为了保暖,用扎腿布把小腿也勒起来,一旁看着比平时更显得精神。他倒剪着双手,眯缝着双眼,离得有两米远距离,边打量边指挥:左边贴高了,再低点,对齐,对齐,好,贴上吧!
在乡下,门心多半贴的是门神,祈求祐护四季平安。常见的有,左边手持大刀的红脸关公,右边手持长矛的黑脸张飞;或者背锏的秦琼和手持长刀的尉迟恭;或者骑马的赵云和挺枪的马超……
门框上多半是祝福、祈盼平安的对联。像“岁岁皆如意,年年尽平安”、“户户金花报喜,家家紫燕迎春”、“春风送春处处春色美,喜鹊报喜家家喜事多”、“南疆雨北国风风调雨顺,东海龙西山凤凤舞龙飞”……
门楣贴了横批,多是“万象更新”、“四季如春”之类。
挨着门楣上方是门滴溜,上边写有三个“春”或倒贴的“福”字。
老百姓朴实,在日常生活的用具上都贴了春联。如驾子车的车架上贴上自己写的“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粮囤上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灶屋里贴“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大门口贴“身体健康,出门见喜”……乡亲们以春联的形式表达着朴素的情感,展望新的年景,寄托新的希望。
家家户户大红的春联,映衬得整个村子充满喜庆、吉祥的节日气氛。
放鞭炮
年三十就是小年了,沿袭着千年不变的吃饺子放鞭炮的习俗。挨近中午,鞭炮声就一阵急似一阵。母亲总是把放炮的任务交给我,她和奶奶早已包好了饺子,只等我燃放鞭炮以后下到锅里。我把两千响的浏阳鞭炮拆开封纸,一头挂在小树杈上。从灶房找来烧火棍,小心翼翼地点燃鞭炮,药捻子嗤嗤地冒着火花,我扭头跑开。瞬间,“噼哩啪啦——咚”, 鞭炮声中夹杂着雷子震耳的声响,与四下里的鞭炮声交融在一起,刺鼻的火药烟味充溢着院落。
家狗吓得缩了头,夹着尾巴躲进窝里。鸡们不安地尖叫着,急急地飞上墙头。
父亲也从城里赶回来过年。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加上我们姊妹几个,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品着醇香的陈年老酒,其乐融融,幸福和欢乐写在每位亲人的脸上。年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其实这时候吃的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亲人们在一起团团圆圆、快快乐乐。
除夕夜,在如豆的煤油灯下,奶奶和母亲仍忙碌着包饺子,以备初一早上吃。饺子是白菜细粉大肉馅的,奶奶擀皮母亲包。奶奶常说,饺子不要样,来回捏三趟。母亲和奶奶你一句我一句的唠,多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也有对新年的憧憬。爷爷坐在炕头给我讲“年”的故事。我一边听,一边想象着“年”的模样,它一定是三头六臂,样子丑陋,力大无比,无恶不作,专门祸害百姓。“年”怕响声,放炮可以让“年”进不了村子……爷爷的故事虽好,可我精力不济,小孩子不禁熬,听得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很快就要睡着了。直熬到三星正南,爷爷晃醒我,快去放“关门炮”,小心“年”来了!我打了一个激灵,点了盘“小豆杂”扔在门外边,伴随着稀稀落落的炮响,这一年便画上了句号……
年初一早晨,我还在睡梦中,爷爷便把我喊起。此时乡间万炮齐鸣,炮声比年三十愈烈。我们这地方有个说法,初一这天谁家起得早,寓意着谁家这一年都要交好运,顺顺当当。我朦胧着双眼,荷衣起来,匆匆放了盘“开门炮”。过一会,母亲又催我放鞭炮下饺子,在周围彼起此伏的炮声中(meiwen.he.cn),把新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