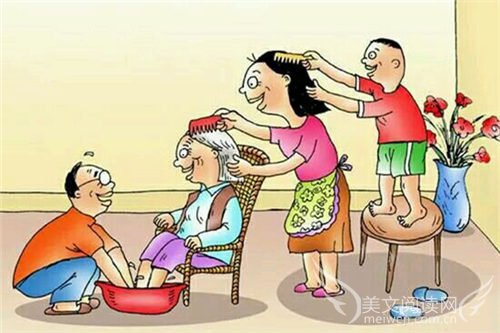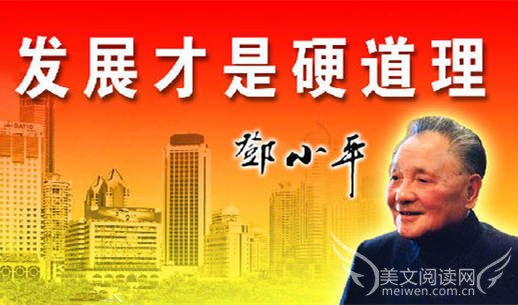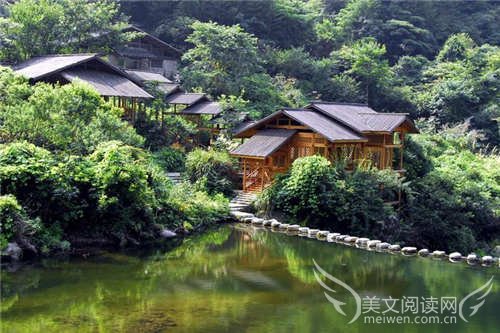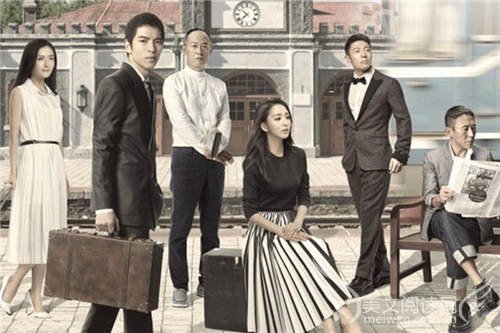致作者:陈新民散文印象
《寻找那种清澈的感觉》中的许大奶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非常不起眼的小人物,文中对她善良朴实的本性的展示竟是那样从容而又令人震撼。“她那昏花的双眼因滚动着泪花透闪出一种难以言述的清澈”,“我确信,世上最清澈的水不在泉,不在河,不在湖海,而在同情和爱心凝成的泪。”是啊,在那艰难岁月,一个飘泊孤寂的“叛徒的儿子”如果没有许大奶奶:“娃子,人是打截截活的,太阳总打人家门前过哩,再艰辛也要把心落到宽展处好好苦呵……” 这样贴心的慰藉和那清澈同情的泪花,又怎么能够熬过那放逐的岁月?正是“乡村以它广大的胸怀,淳朴的乡情接纳了我,塑造着我”,才赋予了“我”远走千里万里也忘不了的根,永葆百性情怀的本。
三
这里,还想谈谈《隐伏刘家营子》。这篇低姿态显身的短文,能从全国强手如林的报人散文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国第二届报人散文奖(而且是唯一的全票获奖作品),本身已引人深思:文学表现中,有时候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
去年二月,从《美文》上第一次读到这篇作品,立即感到一种震撼,掩卷即生不吐不快之意。文中红与黑、邪与正、死与生、远与近、恶与善、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放眼所见的现实,如此对立统一地交汇在一起,给人心灵的纠结难以平复。那“一片红”的“红”罩着的是“红色恐怖”下的黑暗,弹丸之地的酒泉,只是“全国一片”的缩影。你笔下“给父亲架‘土飞机’、拳擂、脚踹、扇耳光、皮带抽……”一系列暴行,岂止是“父亲”个人的灾难!那是我们共同经历的暴政,是整个民族的不堪回首的劫难!面对摧残“父亲”不改初衷掷地有声:“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那是知识分子共赴国难的壮举。我可以否认自己,但我能否认这段历史吗?”他公然表示“不后悔参加青年远征军,不后悔参加中共地下党,不后悔上大学”。闻讯表舅轻生,“父亲”表示自己“绝不会自杀”!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内在的精神基因:“士可杀而不可辱”和“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不苟活与不轻生两种生命价值观的体现,前者虽然消极,但他们同样是对生命意义的执着,对崇高的追求。
红色恐怖能彻底泯灭人性吗?你在文中作了否定的回答:在大难临头、无处可躲的时候,是远在宁夏中卫多年未走动的远亲不仅收留了落难的父子,而且受到了街坊邻里的礼遇……在中卫刘家营子,“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曾是“一城房屋半城庙”的佛教兴盛地中卫,偷偷念佛公开吃斋的姑奶,半公开的“黑市”交易,天天吃大米白面的富足生活和“我”从没吃过的好饭食,还有芮姓的地主亲戚有尊严地设宴摆酒走亲串友,中卫中学“被罢官的校长天天在收发室下棋,棋子拍得啪啪响,围观的人笑声不断……”
在这被红色恐怖遗忘的地方,莫非有佛光筑起了无形的防火墙?其实,求真向善爱美之心,是牢牢筑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防火墙,那是假恶丑凭借着再大的势力也无法占据的高高的灵山。“一片红”的神话在这里破灭了,促使文化专制决堤的力量在积蓄着……紧接着《隐伏刘家营子》,你又在推出了《远去的狼爷》《封口》等力作。很快,这些表现文革的系列作品被多家报刊转载。作品启示读者在回顾过去的同时,帮助读者换一个角度审视现实。不由使人们想起今年“两会”上,温家宝关于防止文革重演的警示。
中国第二届报人散文奖颁之日,西安晚报以《向高贵的心灵致敬》为题,报道颁奖典礼和获奖作者的感言。你说:“我写文革中的经历,缘于文化专制下的艰难生存及深度创痛。……暗夜里闪烁的人性光辉,使真的更真,善的更善,美的更美,那是不能复制的。高压下骤变的人性扭曲,使假的更假,恶的更恶,丑的更丑,而这些,却很有可能重演。似曾相识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不乏“能见度”……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提请人们重视。所以,无论回音大小,我愿继续发声。”你的“发声”蕴含的人文关怀内涵,显示的文化自觉张力。证明你无愧于西安晚报传达的敬意。
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美感来自语言的魅力。你的一些作品如《阳关渐近故乡远》、《第一缕春风吹动谁》、《仰之弥高的背影》、《重修文昌阁赋》等,表现对象多是历史文化事件和文化人,语言洗练优雅,很显文字功力。比如,你写刀,阳刚之美呼之欲出:“以刀寄情,感叹不遇,呼唤道义,抒发理想是古典诗词常用的表现手法,——‘何意百炼钢,化做绕指柔’的哲理内涵;‘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意茫然’的浩远情怀;‘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的超拔境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古代文人志士的精神追求和忧患意识,”刀光剑影折射的“清贤达志、英雄末路、奸佞走红”众生相。使读者对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那些委婉地表现心境的语句,以柔美秀丽的意象,拂动读者心弦。如《隐伏刘家营子》的结尾,“湖面辽阔,水天一色,一只白鹭悠悠掠空,三两湖鸥嘎嘎击水,群群野鸭滑动细长的波纹……”眼前悠闲的平静无法抚平作者内心的翻腾与惆怅,那已深埋湖底的刘家营子,那人,那集市,那跌水坑冰面下的游鱼,还有那年节的景象,丰美的饭食……,那所有的质朴、纯真、宽厚、仁爱该不会沉入湖底吧?那曾经的荒诞岁月,不堪回首的劫难,该不会淡忘吧!那“细长的波纹”不正是无尽的遐想吗……和许多读者一样,我以为更能打动人的,是你从底层生活中采掘提炼出的民众语言。那份鲜活、那份深刻、那份幽默使你的作品格外“好看”,看后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城郊有个垫圈房》中独眼马爷说的:“剑里最锋锐的是舌剑,狼里最狠毒的是绵狼”,话如利刃,剖开社会生活的表层,直指你不曾见识深度。你还用“弯了弯是个榆棍,怂了怂是个男人”揭示无论地位多么地下,都要活出个人样来。这位抗战老兵的尊严观是如此鲜明又如此感人,不仅使你难以忘怀,还因你的作品感动了无数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