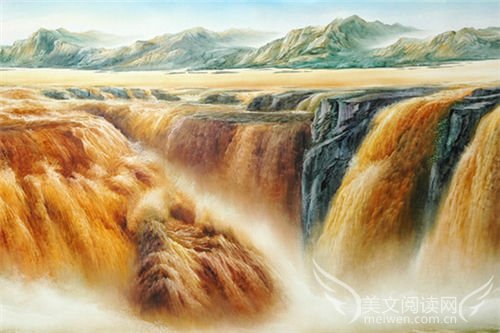沉沦的故乡,永恒的家园
1
我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并由此曾一度痴迷过文学创作,也断断续续写过一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后因“改行”从事行政工作,白天总有忙不完的琐碎事,晚上则穷于应酬,慢慢的把读书写作丢弃一边。幸好从事的工作从未离开过土地、村庄和农民。多年来,我几乎跑遍了全广西所有的市、县,亲眼目睹了土地、村庄和农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革,更亲眼目睹了地处偏僻山区的老家界岭村一步步走向“沉沦”的过程,不知是喜还是忧的感触令人难以释怀,并促使我在工作之余不时拿起笔来,最终形成了一些文字,多年积累下来,居然已有不少。这次本意是把自己参加工作以来所写的各类内容的文字集中起来出个集子,不想汇总后发现以老家界岭村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文字占了大多数,为此友人们建议,与其把所有的文字都汇集起来,出个大杂烩的集子,不如专门出个以反映老家历史变迁的集子或许更有现实的意义。我听从友人们的建议,选取了其中的31篇,并把书名定为《回望故乡》。
“回望”,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回顾,回头看”或“回顾,回头远看。”之所以把这个集子定名为“回望故乡”,自然是因为这个集子的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回顾我的老家界岭村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小部分改革开放后父老乡亲们外出打工的事情。我之所以这样“布局谋篇”,自然有个大胆的设想:通过对我老家界岭村的记载,见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村庄的环境情况,以及村庄的发展和“衰落”的一些轨迹。
或许有人会说,你算老几,竟敢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界岭村比肩整个的中国村庄,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不怪有人会这么说。因为界岭村的的确确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山区小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甲天下,成为中国村庄发展的时代标杆,也不像一些至今尚在黑暗中摸索(还没通电)的更为偏僻封闭的山村那样家徒四壁、食不果腹。然而,正因为界岭村既不最富裕也不最贫穷,而是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中最普普通通的一个,才更具有代表性。
2
据相关部门最新统计数据,在2000年时,我国尚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年消失9万个。由于数字如此的触目惊心,我一度十分关注相关部门公布的信息和媒体的报道,看到不少诸如“百年老村只剩一个老人”、“‘末代村民’相依相守”、“九成土坯房即将倒完”、“葬礼难找抬棺人”、“空心村:不亡而待尽”,等等有关村庄即将消失的信息和报道。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村庄的消失速度正在进一步加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曾给消亡的村庄这样定义——如果一个村庄剩的户数和人数到达这样一个状态:红白大事凑不起办事的人手,现有适龄年轻人在村里找不到对象,后辈年轻人再不愿回村居住,那么,这个村庄也就“不亡而待尽”了。我老家界岭村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这自然首先是由于它地处福绵、陆川两县(区)交界的山区角落的原因。或许有人不相信也不理解,尽管界岭村离远在南宋时就有“岭南都会”之称的玉林市城区仅仅只有不足20公里的路程,但至今仍只有一条狭窄的机耕路将它与外界相连。其实我也不理解,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村村通公路工程”已实施这么多年,离城区如此近的界岭村至今尚未通公路。
曾有媒体对正在消失的村庄做过调查,村庄消亡的主要原因是:年轻一代外出打工(据统计部门的数字,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亿人);种田效益长期低下,农业凋敝,经济上没有出路;大量撤并农村中小学致父母外迁陪读;土地被征收征用。对照界岭村,年轻人的确大部分已外出打工,但依然有部分留在村里发展;农产品市场很不景气,价格极其低下,但留在村里的家家户户依然坚持种田,粮食还能自给自足;村里的小学依然存在,小孩子们还可以就近读书;由于有一条铁路和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村里,土地被征收了一部分,但基本上都是山地,对生产生活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此外,村里还有不少的砖瓦房子,这些房子尽管大部分已十分陈旧了,但还有不少人住在里面。变化最小的是村前屋后的田地,这块是钟家的那块是尧家的、马家的、邓家的,分田到户以来,一直没变化过,村民们依然在种植水稻、玉米、蔬菜等等。或许是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的缘故,界岭村的发展不算太快,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昔日的面貌,保留着一份古朴、宁静的形象。如果它在城市边缘,或许早已被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所吞噬,同时它不临江,山虽然一座接一座的,但不秀丽,所以没有被征去盖临水别墅,或者开发成人来熙攘的旅游景点。
然而尽管如此,界岭村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最明显的就是“人去楼空”。村主任告诉我,界岭村现在共有92户人家、444人,留在老家的已不足200人,大半中青年人已进城打工。为了孩子们有个好的未来,他们大都把儿女们一并带到了身边。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见得混得有多好,但终究要比在村里过得殷实。我生于界岭村长于界岭村,对父老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比较了解,十分明白“洗脚进城”是他们的一种历史性选择。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田种地,常常是入不敷出,实在是没有什么前景。此外,村里的环境条件确实无法和城里比,别的不说,不通公路就是很苦命的事,那条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机耕路经过几十年的碾压,实在是破烂不堪,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够折腾人:晴天一路尘土飞扬,让人感觉呼吸都困难,雨天则一路黄泥浆,不管走路还是骑车都“寸步难行”。除了不通公路,村里也不通自来水,每家每户至今喝的依然还是自家挖的井水。最令年轻人不习惯的是卫生,特别是没有专门的卫生间,每次上茅厕解决大问题都必须经受成群蚊子的疯狂肆虐。由于城乡的巨大落差,走出去的乡亲除非迫不得已极少再回来,有活路的大都还会想方设法把家人和亲戚一并带出去,所以进城打拼的有不少属于整个家庭的,部分只留下老人看护家园。
此消彼长,随着“洗脚进城”家庭和村民的增多,“人去楼空”已成为界岭村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由于没有人气,房子破败得异常的快。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泥砖屋。年前,我曾多次回到界岭村,所到之处映入眼帘的只能用惨不目睹来形容:起码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泥砖屋已崩塌,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的老宅随处可见,屋顶、墙壁四穿八漏、摇摇欲坠的泥砖屋比例也不少。再看那些红砖青瓦小洋楼,虽然大多保存完整,基本没有崩塌的,但整个颜色陈旧、墙面斑驳脱落的败落景象也是非常的明显……可以说村里最鲜亮的房子就属各个家族的祠堂了,由于红白喜事和每年的过年都要用到,不管贫富,不管要花多少钱,人们都会慷慨解囊,及时进行修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祠堂,已成为了许多外出打工者尤其是一些已没有老房子的游子们铭记心头的标志性建筑。只是,因为长久无人进出,祖先的牌位大多已被蜘蛛网占领。每次用到的时候,都得进行一番清洁打扫。
我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并由此曾一度痴迷过文学创作,也断断续续写过一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后因“改行”从事行政工作,白天总有忙不完的琐碎事,晚上则穷于应酬,慢慢的把读书写作丢弃一边。幸好从事的工作从未离开过土地、村庄和农民。多年来,我几乎跑遍了全广西所有的市、县,亲眼目睹了土地、村庄和农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革,更亲眼目睹了地处偏僻山区的老家界岭村一步步走向“沉沦”的过程,不知是喜还是忧的感触令人难以释怀,并促使我在工作之余不时拿起笔来,最终形成了一些文字,多年积累下来,居然已有不少。这次本意是把自己参加工作以来所写的各类内容的文字集中起来出个集子,不想汇总后发现以老家界岭村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文字占了大多数,为此友人们建议,与其把所有的文字都汇集起来,出个大杂烩的集子,不如专门出个以反映老家历史变迁的集子或许更有现实的意义。我听从友人们的建议,选取了其中的31篇,并把书名定为《回望故乡》。
“回望”,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回顾,回头看”或“回顾,回头远看。”之所以把这个集子定名为“回望故乡”,自然是因为这个集子的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回顾我的老家界岭村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小部分改革开放后父老乡亲们外出打工的事情。我之所以这样“布局谋篇”,自然有个大胆的设想:通过对我老家界岭村的记载,见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村庄的环境情况,以及村庄的发展和“衰落”的一些轨迹。
或许有人会说,你算老几,竟敢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界岭村比肩整个的中国村庄,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不怪有人会这么说。因为界岭村的的确确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山区小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甲天下,成为中国村庄发展的时代标杆,也不像一些至今尚在黑暗中摸索(还没通电)的更为偏僻封闭的山村那样家徒四壁、食不果腹。然而,正因为界岭村既不最富裕也不最贫穷,而是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中最普普通通的一个,才更具有代表性。
2
据相关部门最新统计数据,在2000年时,我国尚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年消失9万个。由于数字如此的触目惊心,我一度十分关注相关部门公布的信息和媒体的报道,看到不少诸如“百年老村只剩一个老人”、“‘末代村民’相依相守”、“九成土坯房即将倒完”、“葬礼难找抬棺人”、“空心村:不亡而待尽”,等等有关村庄即将消失的信息和报道。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村庄的消失速度正在进一步加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曾给消亡的村庄这样定义——如果一个村庄剩的户数和人数到达这样一个状态:红白大事凑不起办事的人手,现有适龄年轻人在村里找不到对象,后辈年轻人再不愿回村居住,那么,这个村庄也就“不亡而待尽”了。我老家界岭村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这自然首先是由于它地处福绵、陆川两县(区)交界的山区角落的原因。或许有人不相信也不理解,尽管界岭村离远在南宋时就有“岭南都会”之称的玉林市城区仅仅只有不足20公里的路程,但至今仍只有一条狭窄的机耕路将它与外界相连。其实我也不理解,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村村通公路工程”已实施这么多年,离城区如此近的界岭村至今尚未通公路。
曾有媒体对正在消失的村庄做过调查,村庄消亡的主要原因是:年轻一代外出打工(据统计部门的数字,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亿人);种田效益长期低下,农业凋敝,经济上没有出路;大量撤并农村中小学致父母外迁陪读;土地被征收征用。对照界岭村,年轻人的确大部分已外出打工,但依然有部分留在村里发展;农产品市场很不景气,价格极其低下,但留在村里的家家户户依然坚持种田,粮食还能自给自足;村里的小学依然存在,小孩子们还可以就近读书;由于有一条铁路和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村里,土地被征收了一部分,但基本上都是山地,对生产生活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此外,村里还有不少的砖瓦房子,这些房子尽管大部分已十分陈旧了,但还有不少人住在里面。变化最小的是村前屋后的田地,这块是钟家的那块是尧家的、马家的、邓家的,分田到户以来,一直没变化过,村民们依然在种植水稻、玉米、蔬菜等等。或许是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的缘故,界岭村的发展不算太快,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昔日的面貌,保留着一份古朴、宁静的形象。如果它在城市边缘,或许早已被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所吞噬,同时它不临江,山虽然一座接一座的,但不秀丽,所以没有被征去盖临水别墅,或者开发成人来熙攘的旅游景点。
然而尽管如此,界岭村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最明显的就是“人去楼空”。村主任告诉我,界岭村现在共有92户人家、444人,留在老家的已不足200人,大半中青年人已进城打工。为了孩子们有个好的未来,他们大都把儿女们一并带到了身边。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见得混得有多好,但终究要比在村里过得殷实。我生于界岭村长于界岭村,对父老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比较了解,十分明白“洗脚进城”是他们的一种历史性选择。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田种地,常常是入不敷出,实在是没有什么前景。此外,村里的环境条件确实无法和城里比,别的不说,不通公路就是很苦命的事,那条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机耕路经过几十年的碾压,实在是破烂不堪,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够折腾人:晴天一路尘土飞扬,让人感觉呼吸都困难,雨天则一路黄泥浆,不管走路还是骑车都“寸步难行”。除了不通公路,村里也不通自来水,每家每户至今喝的依然还是自家挖的井水。最令年轻人不习惯的是卫生,特别是没有专门的卫生间,每次上茅厕解决大问题都必须经受成群蚊子的疯狂肆虐。由于城乡的巨大落差,走出去的乡亲除非迫不得已极少再回来,有活路的大都还会想方设法把家人和亲戚一并带出去,所以进城打拼的有不少属于整个家庭的,部分只留下老人看护家园。
此消彼长,随着“洗脚进城”家庭和村民的增多,“人去楼空”已成为界岭村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由于没有人气,房子破败得异常的快。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泥砖屋。年前,我曾多次回到界岭村,所到之处映入眼帘的只能用惨不目睹来形容:起码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泥砖屋已崩塌,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的老宅随处可见,屋顶、墙壁四穿八漏、摇摇欲坠的泥砖屋比例也不少。再看那些红砖青瓦小洋楼,虽然大多保存完整,基本没有崩塌的,但整个颜色陈旧、墙面斑驳脱落的败落景象也是非常的明显……可以说村里最鲜亮的房子就属各个家族的祠堂了,由于红白喜事和每年的过年都要用到,不管贫富,不管要花多少钱,人们都会慷慨解囊,及时进行修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祠堂,已成为了许多外出打工者尤其是一些已没有老房子的游子们铭记心头的标志性建筑。只是,因为长久无人进出,祖先的牌位大多已被蜘蛛网占领。每次用到的时候,都得进行一番清洁打扫。